那时候,我刚从铁匠铺里出来,浑身还冒着热气。老铁匠用他粗糙得像树皮一样的手,最后一次抚摸我的剑身,眼神里有种我看不懂的复杂。他喃喃自语:“好材料,好火候,剩下的,就看你的命了。”然后,我就被交到了一个年轻人手里。
那双手,坚定、有力,掌心滚烫。他叫卡尔,一个初出茅庐的冒险者。他看着我,眼睛里有光,那种光是能把我冰冷的钢铁都点燃的。他轻轻挥动我,破空声清脆、锐利,像一声短促的鹰啼。他惊喜地对老铁匠说:“真是一把好剑!”
我的辉煌岁月,就此开始。
卡尔带着我,走遍了大陆的每一个角落。我们在晨曦森林里砍断过缠绕的魔藤,剑锋过处,绿色的汁液飞溅,带着草木的腥气;我们在北部冰原上,劈开过雪狼坚硬的头骨,“铛”的一声脆响,伴随着狼群凄厉的哀嚎;我们也曾在幽深的地穴里,与那些披着厚重岩石甲壳的洞穴虫搏斗,火星四射,每一次撞击都让我的身体发出兴奋的嗡鸣。
那时候,我的身体是完美的。笔直的剑身,寒光凛冽,像一道凝固的闪电。剑刃薄而锋利,吹毛断发。卡尔每一次挥动我,都感觉我们心意相通。我不是他手中的工具,我是他手臂的延伸,是他意志的体现。战斗时,我能清晰地感受到他肌肉的每一次绷紧,步伐的每一次变换。我们一同呼吸,一同进退。
我的身上,渐渐留下了痕迹。那不是瑕疵,那是我的勋章。靠近剑格的地方,有一道深深的凹痕,那是挡下兽人首领的重斧时留下的,那次,卡尔的虎口都被震裂了,血顺着我的剑柄流下来,温热温热的。剑尖稍微有一点点不易察觉的弯曲,那是一次惊险的突刺,穿透了龙裔战士的鳞甲后,撞在了后面的岩石上。剑身上布满了细密的划痕,像岁月的年轮,记录着每一次格挡、每一次交锋。
卡尔常常在篝火旁,用软布细细地擦拭我,手指拂过那些伤痕,眼神里是骄傲,是珍惜。他从不觉得我丑,他说,这些是我和他一起活过的证明。那时的我,虽然身上布满战斗的痕迹,但我的“魂”是完整的,是锐气十足的。每一次出鞘,都带着一往无前的决绝。
转折发生在那场与深渊魔物的恶战。
那是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可怕生物,浑身流淌着粘稠的黑暗,能腐蚀一切。为了救下被逼入绝境的卡尔,我用尽全力,迎头劈向了它挥来的、裹挟着腐蚀能量的触手。那感觉,不是金属碰撞,更像是砍进了一摊粘稠的、极具侵蚀性的酸液里。
“嗤——”
一声令人牙酸的声音。我感觉到一股冰冷彻骨的恶毒能量,瞬间侵入了我的身体。剧痛!那不是物理上的断裂,而是生命本源被污染、被侵蚀的痛楚。剑身上,靠近刃口的地方,被腐蚀出了一道难看的、如同被啃噬过的缺口,周围的金属也失去了光泽,变得灰暗、斑驳。
战斗结束后,卡尔看着我身上的伤口,沉默了许久,眼神里满是心痛。
“别担心,老伙计,”他沙哑着嗓子说,“我会把你修好的。”
他带着我,找到了王城里最有名的铁匠,据说他能让断剑重生。
修复的过程,我至今不愿详细回忆。那是在一个高温的熔炉旁,老铁匠(不是创造我的那一位)审视着我的伤口,摇了摇头。“腐蚀得太深了,普通的锤炼不行,必须用‘融金术’,补入新的材料,重塑这一部分。”
我被固定在铁砧上,看着烧红的烙铁和新的、闪着亮光的金属块靠近我的伤口。当那滚烫的、陌生的金属熔液覆盖在我的伤口上时,我发出了一声只有自己能听到的哀鸣。那不再是战斗的灼热,而是一种毁灭与重铸的煎熬。剧烈的锤打落下,每一次撞击,都仿佛在将我原有的记忆、那些与卡尔并肩作战刻入身体的记忆,一锤锤地砸散、砸碎。
新的金属,强行融入了我的身体,填补了那个缺口。然后是被放入冷水中淬火,“刺啦”——巨大的温差让我几乎晕厥。最后,是打磨。砂轮在我身上飞速旋转,磨掉了那些斑驳的腐蚀痕迹,也无情地磨掉了周围那些承载着记忆的细小划痕。
当一切结束,我被交回到卡尔手中时,他眼前一亮。
修复处,光滑如镜,闪着均匀而陌生的金属光泽,和周围我那身布满历史痕迹的剑身形成了鲜明又刺眼的对比。整把剑看起来,几乎像新的一样,至少,那个致命的伤口不见了。
“太好了!修得跟新的一样!”卡尔高兴地说,像以前那样,习惯性地挥动了我一下。
就是这一下,我们都感觉到了不对劲。
风声不对。
以前我破开空气,是清脆、锐利的“嗖”声,带着一种一往无前的穿透力。而现在,声音变得有些沉闷、有些……滞涩。仿佛空气不再是需要被切开的对象,而是变成了粘稠的胶质,在阻碍着我。
卡尔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,他皱了皱眉,又试了一次。这次他用了更大的力气。结果还是一样。那种人剑合一、如臂使指的流畅感消失了。我感觉到沉重,一种从修复处蔓延开来的、内在的沉重。仿佛那一块新补上的金属,不仅仅是一块金属,它是一块没有灵魂的、死气沉沉的肉,长在了我的身体里。
它无法理解卡尔的意志,无法与我这把老剑的其余部分协同振动。它就在那里,沉默地、固执地存在着,像一个不和谐的音符,破坏了我整个身体的共鸣。
我的性能,无可挽回地下降了。
以前,卡尔能用我使出精妙的“闪电三连刺”,现在,同样的招式,速度会在我传递到剑尖时,被那个修复处微妙地阻滞一下,变得不再连贯。以前,我能凭借完美的平衡和锋锐,轻易地格开敌人的攻击并顺势反击,现在,格挡时,力量的传导会在修复处产生一丝不易察觉的“卸力”,让卡尔的反击慢上半拍。
这半拍,在生死搏杀中,是致命的。
卡尔尝试着去适应。他调整发力方式,调整战斗节奏。但我们之间那种多年形成的、无需言说的默契,被打破了。他挥剑时,开始有了犹豫,因为他无法再百分之百地预判我的轨迹和反应。而我,更是痛苦。我能感受到他的努力,他的不适,我却无能为力。那个修复处,像一道无形的屏障,隔在了我和我唯一的主人之间。
后来的战斗,变得艰难。我们不再是无往不利的组合。一次面对几个普通的山贼,放在以前,卡尔轻松就能解决。但那次,因为一次格挡后的反击慢了那关键的半拍,他的手臂被划开了一道口子。虽然不深,但鲜血流出时,我感觉到一种彻骨的耻辱。
我听到他在夜深人静时,对着篝火低声叹息:“是不是……修复得不对?还是我自己的问题?”
不是你的问题,卡尔。是我的问题。我在心里呐喊,但你听不见。
我不再是他那柄无所不能的利刃了。我成了一把需要他小心翼翼使用的、普通的剑。他依然爱护我,擦拭我,但眼神里那份毫无保留的信任和依赖,渐渐被一种复杂的、带着惋惜和审视的情绪所取代。
我知道,他后来又定制了一把新的剑,由矮人大师打造,用了更好的材料,更精良的工艺。那把新剑,锐利、轻快、平衡完美。他出门进行重要的任务时,开始更多地带着那把新剑。
我被他恭敬地、带着一丝仪式感地,挂在了他书房墙壁最显眼的位置。
他常常会看着我,对来访的朋友介绍说:“这是跟了我最久的老伙计,救过我的命。”朋友们会投来敬佩的目光,称赞我的历史和那些依旧可见的、修复处旁边的古老伤痕。
我成了一件展品,一个象征,一段被缅怀的历史。
他们看到的,是一把造型古朴、有着光荣伤痕的剑。他们看不到的,是我身体里那个格格不入的“补丁”,以及我那被永远改变了的、不再完整的“魂”。
阳光从窗户照进来,洒在我身上,修复处那块特别光滑的地方,反射出刺眼的光。很亮,但没有温度。
我依然是一把剑。只是,我再也唱不出那首清脆、锐利的战歌了。
那把矮人打造的新剑,就挂在我不远处,它沉默着,却仿佛散发着年轻的、跃跃欲试的锐气。而我,只能在这墙上,静静地,回忆着我和卡尔在风里、在雨里、在血与火里,那段浑然一体、锋芒毕露的黄金岁月。
那才是我,真正活过的样子。
未经允许不得转载:今典生活 » 内容均为网友投稿,不排除杜撰可能,仅可一观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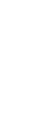 今典生活
今典生活
热门排行
阅读 (29)
1市场调研助理:协助项目的问卷整理阅读 (27)
2曾共看的日落,成单人余晖阅读 (25)
3扫码领洗发水,收到后是小瓶装阅读 (25)
4在跨境电商做选品:从踩坑滞销到爆单的选品逻辑阅读 (23)
5代买限量零食黄牛发错口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