手指触到信封的瞬间,胸口像被什么轻轻撞了一下。七年了,自从他去了那个需要倒三小时时差的城市。
我没急着拆。把菜放进厨房,洗了手,在窗边的旧沙发坐下。午后的阳光斜斜地照进来,灰尘在光柱里慢慢打着旋儿。我用小刀小心地裁开信封,怕伤着里面的每一个字。
信纸是米黄色的,有点厚度,摸起来有细微的纹理。展开时,淡淡的墨水味飘出来——他还是用那款蓝黑墨水,我知道的。
“见字如面。”开头这样写。
就这四个字,让我的眼眶一下子热了。有多久没听到这句话了?又有多久,我们只是在手机屏幕上发送那些转眼就会被淹没的快捷信息?
他说,这个周末他去了海边。不是我们曾经一起去过的那个,是另一个更偏僻的海滩。他在信里描述海浪的声音——“像大地在缓慢呼吸”,还说他捡到一枚特别的贝壳,螺旋状的,已经放在信封里一起寄来了。我这才发现信封底确实有个小东西,轻轻倒出来,是一枚小小的海螺,白底带着淡褐色的纹路。
我把海螺贴在耳边。
真的能听见海的声音,呜呜的,遥远的,像从另一个海岸线穿越千山万水而来。那一刻,我好像看见他独自站在海滩上的样子,风掀起他的衣角,他弯腰拾起这枚贝壳,然后想到要寄给我。
信写了整整三页。他说上个月感冒了一场,不严重,但让他想起大学时我给他熬的姜汤;说最近在读一本很旧的诗集,在二手书店偶然淘到的,里面有一首关于离别的诗,让他发了很久的呆;说公寓楼下的桂花开了,香气能一直飘到他的五楼,就像我们以前住的那个带院子的一楼,那棵我坚持要种下的桂花树。
读到这里,我抬头看向窗外。我们曾经的小院早已不属于我们,但那棵桂花树应该还在吧,这个季节,也该开花了。
他说这些时,语气平静,像在和一个坐在对面的老友聊天。没有抱怨距离,没有诉说辛苦,只是这样淡淡地讲着生活里的小事。可正是这些小事,这些只有我们彼此才懂的细节,让我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下来,在信纸上晕开一小片模糊的蓝。
我想起我们刚分开那会儿。那时候联系多方便啊,视频通话一打就是两三个小时,可挂断后反而更觉得空落。屏幕那头的他那么近,又那么远。后来我们都累了,渐渐变成了几天才联系一次,内容也精简成“吃了没”“忙不忙”这样的对白。
可这封信不一样。它沉甸甸的,不只是重量,还有时间——他写信的时间,信在路上的时间,我读信的时间。这段时间里,这些字句就真实地存在于某个地方,不像手机信息那样点击即达、转瞬即逝。
信的末尾,他写道:“昨晚梦见回到老房子,你在厨房做饭,我从背后抱住你,你回头对我笑。醒来时,窗外天还没亮,鸟已经开始叫了。忽然很想给你写封信,就用这种最笨的方式。”
最笨的方式。是啊,在这个什么都讲究效率的时代,写信多慢啊。可正是这种“慢”,让每一个字都显得格外珍贵。他是一笔一画写的,每一个顿挫我都想象得出来;我是逐字逐句读的,每一处折痕我都反复抚摸。
我把信仔细叠好,放回信封,又把那枚小海螺放在床头柜上。晚上关灯后,月光照进来,海螺泛着微光。我再次把它贴在耳边,海的声音还在,呜呜的,像在诉说些什么。
后来我给他回信了。也选了厚实的信纸,也用钢笔一字一句地写。告诉他阳台的茉莉开了第二茬,告诉他我发现了一家和他口味的面馆,告诉他最近下雨了,雨打在芭蕉叶上的声音还和从前一样。
写完信,封好,投进邮筒时听到那声轻微的“咚”,心里忽然很踏实。我知道这封信会慢慢走,也许三五天,也许一周,才会到达他手中。但没关系,有些东西是值得等待的,就像他寄来的那封手写信,就像我们之间这份笨拙却坚定的感情。
在这个什么都太快的世界里,我们选择用最慢的方式靠近彼此。而当我再次展开那封已经被我读了无数遍的信,抚摸那些微微凸起的字迹时,忽然明白:见字如面,不只是客套话。在那些笔画的起伏里,在墨色的浓淡里,在信纸的折痕里,我真的看见了他——那个在远方,却一直在我心里的人。
未经允许不得转载:今典生活 » 内容均为网友投稿,不排除杜撰可能,仅可一观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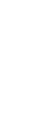 今典生活
今典生活
热门排行
阅读 (34)
1市场调研助理:协助项目的问卷整理阅读 (33)
2曾共看的日落,成单人余晖阅读 (31)
3扫码领洗发水,收到后是小瓶装阅读 (31)
4在跨境电商做选品:从踩坑滞销到爆单的选品逻辑阅读 (29)
5明知没有结果 可心疼还在继续